周克希VS陈村对谈:
逝去的时光是幸福的
本报记者 文敏
 |
| 《追寻逝去的时光1·去斯万家那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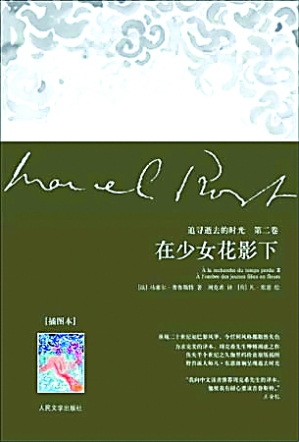 |
| 《追寻逝去的时光2·在少女的花影下》 |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开创意识流文学的里程碑之作,作者马塞尔·普鲁斯特青年时代经常出入上流社会沙龙,父母相继去世后,他痛感“幸福的岁月是逝去的岁月”,开始写作本书。他借助于不由自主的回忆,将逝去岁月的点点滴滴重现在读者眼前,使时间在艺术中得以永存。
翻译家周克希继独自译完普鲁斯特名著《追寻逝去的时光》首卷《去斯万家那边》6年后,再度推出了第二卷译本《在少女花影下》。对此,周克希戏称:“每天都在看普鲁斯特的文字,相处时间长了也需要调剂。”著名作家陈村在此期间一直关注着这部译著的进程,他则为老友向记者解释道:“他还特地去了普鲁斯特住的地方,就是想亲自感受原著中的场景,寻找作者笔下每一处风景,让译文能更忠于原著。”
陈村调侃自己英文不好,想看外国文学就得依靠翻译者,“不同的译者呈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更像是自我创作。”陈村说,“真正的大师是经得起损耗的。”而周克希则说:“对原著的损害是不应该的,要认真。把一仆二主作为标准。”周克希所说的“二主”是指作者和读者,“做译本的时候心里要装着读者。”
周克希:你说老的普鲁斯特译本(《追忆逝水年华》),你可以看到第二册。而更多的人是连一册也看不下去。一方面是普鲁斯特本人的所谓可读性比较差一点。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恐怕也是翻译的问题。如果翻译得比较传神的话,有兴趣的读者还是会看得下去的。
陈村:我觉得读它的主要障碍不是这个,读它的主要障碍是两种情景。我们的生活情景和他的小说里面描写的情景反差太大。我不是说么,读他这本书最好是关在医院里,或者是关起来疗养的时候。没有事情做你就每天读一点每天读一点。平时在一种很烦躁的生活状态中,去读他当然也可以,可读着读着觉得不太对头,就不容易进入这本书的情景。
周克希:我在翻译过程中有时觉得还是挺有共鸣的。昨天正好译到主人公“我”还比较小的时候(这个主人公到底有多少年纪,我们始终都搞不清楚),跟他的外婆一起乘火车到一个小站停下来,看到一个卖牛奶的少女在兜售牛奶。这姑娘长得人高马大,太阳刚刚出来,照书里的描写,又是金光又是玫瑰色。这种情景对主人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翻译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有共鸣,因为这种生活场景多多少少我们是遇到过的。
陈村:前两天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讲读书,我说去读一点外国名著,就是有定论的经典之作。不要去读很多当下出版的书,这种书可能你读了一百本书就找到一两本好的。经过历史淘汰不是方便了吗?人家帮你淘汰好了有定论了,先看这种书。他讲那么我去读原著好吗?我说当然好,假如能够读原著太好了,读译本是不得已的事情。
周克希:翻译总归打折扣的。
陈村:(笑)可能也有伟大的翻译家把它翻译得增色。
周克希:有一种讲法就是比原文还要好。那么……
陈村:问题是,谁要你比原文还要好!哈哈。
周克希:这个当然。但是翻译原文,我觉得最要紧的不是形式,不是形似,而是神似。换句话说,我觉得唯一的标准就是译出法国人读法文原作时的那种感觉,假使中国读者读译文也有这种感觉,或者有这种感觉的百分之八十,我就觉得很好了。法国人读普鲁斯特是一种享受。我有一个朋友,是法国人,我在巴黎高师时,他是读文学的。他来中国,到我家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书,就像我们有时旅行途中带本书一样,那本书就是普鲁斯特。对他们来说,看普鲁斯特就像我们看《红楼梦》一样。
陈村:想看到哪里就看到哪里。
周克希:福楼拜当然是好的,但和他不一样。我觉得普鲁斯特好像更加现代一点,同我们现在更加近一点。《包法利夫人》情节性还是比较强的。普鲁斯特没什么大的情节。他写的一些东西,你说是哲理也好,说是对生活的观察也好,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举个第一卷里的例子,他讲“我们的社会形象是他人思维的产物”。当时译这句话的时候,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译成了“社会人格是他人思维的产物”。第一卷译本书上就是这样的。我现在觉得要是有机会,还是得改成“我们的社会形象”,因为他后面讲的一大段都是这意思。普鲁斯特的特点是他讲了类似警句的东西,后面会有一大段比较形象的东西来说明。那是对的呀。这对你来说可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我们的社会形象,是别人观念的一种组合。他大概是不管小说应该怎么写的。普鲁斯特是非常自信的,他是所谓的内心强大。表面看起来他是一个很谦恭的人,碰到谁都惟恐对方不开心。这种人往往内心很强大。普鲁斯特不是小说写出来起先没有人要吗,但我觉得他确信自己的东西是真正的好东西。
陈村:他在写作的时候也不管人家看得懂还是看不懂,舒服不舒服。我觉得翻译他的作品总有人看的。难说,说不定哪天不对了,一下子就觉得现在这种小说读了都要昏过去的,就读读普鲁斯特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