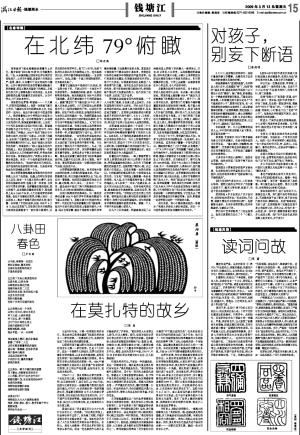|
 |
|
|
2009年3月13日 |
|
||
| 在北纬79°俯瞰 □陈丹燕 |
| 我乘坐的飞机如蜻蜓般扶摇着升上天空,漫步似地飞向北纬78度55分的新奥尔松。于是,从未被碰触过的冰雪世界在我面前徐徐展开。从天空中俯瞰,晶莹的白色荒原庄严、温柔、谦卑,又有着不可思议的纯净与凛冽。山谷中深厚的积雪表面带着沙漠般新月形的蜗旋,那是无数次风暴留下的痕迹。在蓝灰色的大洋上深深龟裂开来的冰盖,以及冰盖断裂的边缘闪烁着的古老的蓝色,从空中看去,它们是如此安详。 我想到的是罗德·阿蒙森——一个大鼻子、面容阴沉的挪威人。他第一次乘坐飞艇升上天空,飞越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上空,也是这样一直向北。他是开辟北极空中航道的第一人。我猜想着他从空中看到这片冰原和大洋时会怎么想:他一定非常想染指它,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染指就意味着征服。上世纪二十年代已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末期,阿蒙森的探险为这个时代划上了完美的句号:1910年他到达了南极点,1926年他用飞艇从空中探索北冰洋,他征服了北极点,又征服了南极点,还征服了北极荒原上的天空,填补了世界地图两端最后的空白点。他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英雄”。我乘坐的小飞机正重复在他当年的航线上,现在这条航线上每天都有一次航班,运送去无人区的极地科学家,科考站的给养和设备。我想起他的话:“我想从来没有人曾如我这般,站在一个与他希望的目标如此截然相反的地方。”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状况。也许他指的是他原想征服北极,但命运却使他成为征服南极点的第一个人。 我从特罗姆瑟峡湾极地博物馆外面的青铜像上认识了他的脸,他脸上的特征很容易让人记住:他有一个又高又长的大鼻子,还有阴沉而坚毅的表情,他脸上没一丝欢愉,也没有任何柔和的阴影。他穿着兽皮做的短袄,肥大的裤子,还有海豹皮缝制的长靴子,那些算得上是从1600年以来,人们在极地穿的标准服装。他岔开双腿站在那里,好像正站在一大块浮冰上。离这个铜像不远处的码头旁,竖立着一块写满了字的纪念碑,纪念1928年6月18日,他从这里起飞,前往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北部的冰原援救昔日一起征服北极领空,后来交恶的伙伴诺毕尔。起飞三小时后,他的飞机消失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上空。他失踪两天以后,诺毕尔被苏联破冰船救起,一直活到1978年。而他,则像一个真正的探险家那样,史诗般地失踪了。 慢慢飞过被他当年染指的白色冰原,我一直努力往下看,不放过任何一个冰雪中不自然的物件,一条椭圆的阴影,或者一块形状特殊的突起物。我试图能发现1928年失事的飞艇残骸,甚至已被冻僵六十年的阿蒙森本人。就像“奥雷尔”号飞艇失踪33年后,终于被人在冰原上找到,人们在别雷岛上找到奥雷尔号上工程师安德烈的尸体,以及他们的遗物。发现尸体的人形容说,安德烈的身体已与冰河以及积雪融为一体,我想阿蒙森也会是这样的。我知道自己这样想是幼稚的,但飞行在当年阿蒙森开辟的航线上,又飞行在当年他失踪的区域,很难完全制止这种猎奇的想象。我幻想着阿蒙森能像他在南极击败的司各特一样,在被冻僵前写下些什么。那个时代的极地探险家,一定觉得这样孤独地死在冰雪中最为完美。他一定不会想到,他的探险已永远打破了冰雪世界的平静和平衡,它从此走向了漫长而不可阻挡的消亡。失去了沉寂和奇寒的冰原和大洋,其间穿梭着商业航班和豪华游轮,这将是多么平淡无奇的地方啊。要是还交错着忙碌的货运飞机和集装箱远洋轮,这就不光是乏味,更令人愤怒。我不知道,要是阿蒙森知道这一切都因他的英雄气而起,他会说什么。 从特罗姆瑟到新奥尔松,冰天雪地中竖立起的纪念碑,大多都与阿蒙森有关。所以一到新奥尔松,我立刻就在峡湾旁认出了他,他是另一尊铜像。他阴沉而坚毅地面向东北方向,越过峡湾,冰川,雪山,一直向北一千公里,就是他当年经历了两个黑暗漫长的北冰洋冬天,在北纬88度找到的北极磁点。 在国王峡湾冰封的海岸边,另一座纪念碑纪念着1926年他和诺毕尔乘坐的挪威号飞艇从这里起飞,探险北极空中航道的伟大事件。不远处至今还保留着高大的飞艇铁塔。他当年在码头旁边的苔原上建造的黄色小木屋,现在也保留着,被各个国家的北极科学考察站围绕着,它是新奥尔松的文物。甚至远在中国的孩子们都会在初中课本里,学到他和司各特在南极争夺探险家的声望的故事。他们的课堂讨论题是:征服极地的好处和坏处。孩子们大多说,征服极地的好处是彰显了人类的勇气和力量,而坏处是也许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个狂热地征服自然的时代,使探险家们做出巨大而虚妄的努力。他们发现了这个世界,也打扰了这个世界。 事情就是这般富有现代的荒诞感:一个人只有到了极地,才会真正爱上这地方。才会知道染指它没有什么好处,坏处也并不是司各特悲壮地死去,或者人类自身的毁灭,而是这地方被毁了。这情形让我想起那些与阿蒙森差不多同时代的作家们,卡夫卡,贝克特,特别是波特莱尔。他们在一张纸和一支笔之间,看出这个世界正在走向令人悲哀的荒诞。 在阿蒙森功成名就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极的冰川已开始融化,古老的冰川向朗伊尔城外的峡湾倾泻着碎裂下来的巨大冰块。在冰舌处,人们能很轻易就捡到本来包含在古老冰块里的石片,石片上面能看到阔叶树叶的化石,那是四千万年左右的古老化石。从那时起,北极将要融化的消息就不绝于耳。开始它好像匪夷所思,后来渐渐被证实。现在则变得紧迫和令人绝望起来了。 沿着他当年的航线,一路上都能看到北冰洋上碎裂的冰盖和冰川上碎裂下来的浮冰,看到湿漉漉的透明冰山,在阳光下闪烁着濒危的晶莹光芒。还能看到产煤的小城。在辽阔的白色雪原上,巴伦支堡像一块黑色的胎记。它的铁道附近都是黑色的,它的街道也是黑色的,它发电厂的烟囱上飘荡着一条长长的黑烟。有人说,在它的建筑物外墙上,巨幅的墙画上,有人抄录了一首诗:“这就是说,在这片你从未走过的大地上,在所有春天的边缘,极地航线令你魂牵梦萦,这冰雪世界,将在你的梦中浮现。”当我掠过巴伦支堡上空的时候,曾希望自己能从照相机的长焦镜头里看到它,我想它是写给阿蒙森的。诗句里好像有种深深的遗憾和温柔的责备,就像一个人不得不否定他最心爱的人。 在几个月后的南极,阿蒙森海出现了从南极冰盖上碎裂下来的最大一座浮冰山,它有25公里长,9公里宽,从南部漂进阿蒙森海。那时我已离开北极。从照片上我看到这块浮动在深蓝色海水中淡蓝色的冰山,和它碎裂飘浮的过程,它看上去就像一块被紧紧捏在手心里过的、令人不安的手帕。 在新奥尔松图书室的外面,有个给社区里的人放松用的大房间,有点像一家人的起居室。那里的墙上装饰着1926年飞艇在孔戈斯峡湾起飞和降落时的大照片。那个下午,我从图书室出来,就看到它们对着如今漂浮着蘑菇形状蓝色浮冰的国王峡湾。粒子粗大的翻拍照片上,能看到庆祝仪式上,神采飞扬的人们和他们的笑颜。那时的人们,以为自己能征服全世界每个角落。由于他们看到了英雄而分外踌躇满志。他们脸上,面颊上,眉眼之间,这儿那儿,都有着那样笑容的阴影。我想照片里被人们簇拥在中央的高个子男人应该就是阿蒙森,他有个大鼻子,虽然没有笑容满面,但却有满脸沉稳骄傲,永往直前的神情。 仅仅过了六十年,事情就已那么不同。当我飞过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一处苔原时,有人告诉我说,这里的地下藏着一个现代诺亚方舟。挪威政府联合了上百个国家,在此建造了一个“末日种子仓库”。里面储藏了地球上所有农作物的种子。为防备地球末日到来时的电力断绝,挪威人特意将这个仓库建立在深入到永冻土下的山洞里,在自然状态下,都可以保持-18℃的低温。那是个为人类末日后准备的仓库,为下一次地球复苏,人类再生时,他们能从这里找到所有优良的农作物种子。按照现在对北极融化后的估计,世界将像《创世纪》中提到的那样,被大洪水洗劫,人类和万物都将灭绝于洪水之中。我的飞机掠过平坦的白色苔原,那里纵横着一条条浅灰色的雪路,我想它们是为向末日种子仓库运送货物而开辟的道路。它们使得那片位于雪山和冰川峡湾之间的苔原好像一只碎裂的玻璃瓶,它已经失去了荒原自身的静谧自在和凄凉阴惨。是的,阿蒙森一定没看到过这样一个碎裂的北极。 此时此刻,我心中蓦地想起他的一番感言:“我想从来没有人曾如我这般,站在一个与他希望的目标如此截然相反的地方。” |
|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