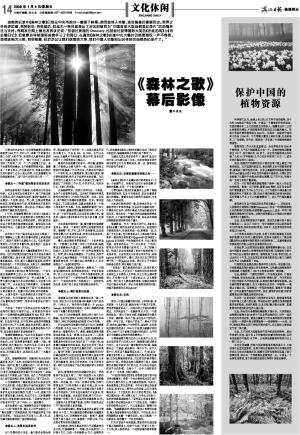|
 |
|
|
2008年1月4日 |
|
||
| 《森林之歌》 幕后影像 ■孙莲莲 |
| 自然类纪录片《森林之歌》已经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落下帷幕。然而曲终人未散,余音袅袅仍萦绕耳边。荧屏之外热评如潮,有赞好的,有挑错的,但却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对这部被称为“中国首部大型自然类纪录片”的热情关注与支持。有网友在网上留言发表议论说:“品尝过美国的Discovery,也品尝过获得国际大奖的《迁徙的鸟》与《帝企鹅日记》,但就是这样被国际美食养刁了的胃口,在遇到《森林之歌》这道中式大餐时仍然要感叹一声不容易。虽然还稍欠火候,有些稚嫩,但亦足以让我们欣喜地大呼,我们中国人也能拍出这样好的自然类纪录片了。” 与观众的兴奋相比,总导演陈晓卿在谈到这部耗资1000万元,历时4年,承载了许多编导无数心血的“大制作”时,却显得出人意料地从容淡定:“这就是我的工作,一部片子拍完了,这段时间的工作结束了,另一个工作也就随之开始。我不会感到特别激动,也不会感到特别兴奋。就像是一个职业军人,打仗就是打仗,你要是问我打仗的时候有什么令人难忘的事,也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卷走了,留下的只有那时的心情……”
●镜头一:“外教”教的很多东西还没用
同样是歌颂我们的森林,但歌颂的方式会有很多。尤其是体现在电视艺术中,我们不能直接告诉观众,我们的森林很美呀,要爱护森林呀,而是要讲一个故事,通过一件小事,让观众看到森林的美,看到森林的可爱,看到森林的不容易和森林面对的严峻形势。通过这些,让观众心领神会到我们最初所说的目的。 4年前,当陈晓卿最初进入纪录片《森林之歌》的创作集体时,对这部纪录片的预想并不是像今天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那时候的定位是介绍我国的森林建设成就、森林现状与森林保护情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行业纪录片。 这样的片子对于编导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找个撰稿写上几集,然后依着内容往上码画面就行了,根本不用费什么脑筋与心思。但如果这样做的话,不仅技术含量很低,连电视的一些独有的表现优势也都会一并失去。 为此,陈晓卿和制片人魏斌都感到并不甘心。然而,他们所设想的拍摄方法此前并没有在国内大规模实施过,没有比照,投资方并不相信他们能够拍摄成功。但是,制片人魏斌反复坚持,投资方答应给他们一个尝试的机会,无形之中,陈晓卿感到自己的肩头压上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当《森林之歌》还在筹划的时候,一个念头就在陈晓卿等主创人员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要像国外的同类题材作品一样完成拍摄”。尽管大部分的编导之前从事的都是人文纪录片的拍摄工作,从未涉及过自然类题材,但陈晓卿却成竹在胸。为了给编导们“恶补”自然类纪录片的拍摄知识,他像中国足球队请外国教练一样,从国外请来一批自然类纪录片的制作大师进行培训。但后来编导们发现,在这方面中国也有着特殊的“国情”,很多老外教的东西我们还没用。 比如有一节课专门讲的是在面对凶猛野生动物的时候如何保护自己。在授课的外国专家——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摄影师Neil看来,野外拍摄是十分危险的,他自己就曾经被熊拍过一巴掌。但是他不知道,在中国,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是比较少的,不只是熊,就连老虎看到人都掉头便跑。编导们每天发愁的不是遇到动物如何自保,而是根本就找不见动物的影子。 陈晓卿幽默地说:“现在在电视画面中看到的那些动物,都是不知道给它们行贿了多少好吃的东西,才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露一下脸。熊和野猪,我们都是用1吨多的玉米,让老乡每天去定点投放,才哄得它们渐渐失去了戒心。”不仅如此,在拍摄过程中,还因此而上演了一出编导失踪记。 这天,陈晓卿照例给一位编导打电话询问拍摄进度,但打了几次,这位编导的手机都是关机。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人就像失踪了一样,和所有人失去了联系。这可把陈晓卿急坏了,他已经走了10多天,按照摄制组的拍摄计划早该回来了,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没了消息,他们工作的地方都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这要是出了事可怎么办。 正在陈晓卿为了摄制组成员的生命安全忧心不已的时候,手机在锲而不舍的反复拨打下终于接通了。那位编导承认错误说,他到秦岭自然保护区是来拍金丝猴的,但找了14天,连猴子的影子都没见着,回去吧,有点不甘心,又怕陈晓卿打电话,来催进度时没法交差,于是索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关了手机一心一意找猴子。 原来是虚惊一场。陈晓卿为这位年轻编导的小小“心机”哑然失笑,随后义正词严地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你再找两天,找不到就放弃这个项目回来吧。”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第2天,这位编导就如愿找到了金丝猴的踪迹。
●镜头二:故事永远是动词
对于电视纪录片来说,最主要的是观众要看。观众就相当于前面的一个1,而意义就是后面的无数个0,可以是100,是1000,也可以是10000,但就算片子再有意义,观众不看,没有前面的那个1,你得到的也只能是0。 像国外的同类题材纪录片一样拍摄,就意味着工作流程上也要与国外一致。因此,《森林之歌》的前期准备工作非常扎实,光剧本创作就花了一年多时间,从文案到剧本,到分镜头脚本,都非常细致清楚,然后才开赴野外实地拍摄。与以前看到什么就拍什么不同,在拍摄之前,编导们就拟订了详细的工作计划,今天拍什么,明天拍什么,大家心里有数。 在陈晓卿看来,纪录片故事化是一个潮流,是合乎市场规律的表现。过去我们拍摄的科普式教育式的纪录片,它的知识性是第一位的。而现在,我们要把它的趣味性提到第一位来。要设置兴奋点,不让观众跑掉,这就必然要求有一个强大的故事作为支撑。为此,陈晓卿给编导们设立了一个标准,就像好莱坞编剧卖剧本时一样,3分钟,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而且必须打动制片商。就这样,《森林之歌》的剧本可以说几易其稿,充满波折。 比如讲金丝猴的那一集,编导最初对陈晓卿说的是,要讲一个秦岭山地野生动物家园的故事。陈晓卿一听,不行,这个不是我要的,这是故事的背景,但不是故事本身,故事永远是动态的,是动词,不是形容词也不是名词。 最后,金丝猴的故事演变成了一个仇杀的故事,一个新猴王和老猴工争夺王位的故事,陈晓卿这才满意地点头通过了。陈晓卿说,别看这是纪录片,其实和拍故事片一样,每种动物都有角色。你看,那只母金丝猴就是一个女演员,风情万种;那只公金丝猴就是一个男演员,目光中还带着淡淡的忧郁,它们就在这山林的舞台上,自发地演出了一场《哈姆雷特》…… 就这样,《森林之歌》的每一集都有了一个简单而明确的故事,热带雨林讲的是一个竞争的故事,长白山红松讲的是一个种子传播的故事,武夷山的竹子讲了一个爱情的故事,而新疆的胡杨讲了一个坚忍的故事,“虽然经过了一些技术性的处理,但我们的立场是为普通观众服务的。”
●镜头三:精打细算的拍摄
陈晓卿在他的博客中幽默地写道:“就工作而言,我认为片子是那些编导和摄影兄弟们的功劳,与我无干,我的角色更像是一个produce manager,即所谓的制片经理。这事儿搁解放前就相当于夹着个算盘的管家。” 1000万元的拍摄经费,曾经让多少同行心生羡慕。但是你知道吗?法国《迁徙的鸟》耗资3500万欧元,BBC的《地球脉动》投资1700万英镑。 和这些国外同类题材的纪录片相比,陈晓卿心里清楚,手头这1000万元,也要勒紧裤腰带,才能拍出一部像样的片子。最初,摄制组想使用高清设备拍摄,但是一算钱,实在是太贵了,只好采用普通的标准机器格式来做。还好,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专家Robert为他们打了一剂强心针,他拿着中国摄影师的设备说,我在全世界用了那么多机器,你们这个机器可是最好用的。在培训课上,编导们看到了这位国际知名的摄影师用DV拍摄的获奖作品《尼亚加拉瀑布的熊》,画质非常清晰,这令他们更加相信,没有不好的机器,只有不好的摄影师;没有不好的剧本,只有不好的导演。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们将这部纪录片拍好的信心。 然而,要做到和国外同类题材纪录片一样的效果可以说是太难了,“我们的投资只有人家的三十分之一,这就注定了我们不可能真正做到像国外一样拍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花钱,而我们常常是拍三四天的镜头只能在电视上放10秒钟”,陈晓卿无奈地说。他们在拍摄过程中是想尽办法节省成本,“其实有些设备我们不是没有,技术也不是没掌握。比如延时拍摄,我们可以从一棵树绿叶拍到开花,可是这样的拍摄需要20天,一直要有人在那里操作机器,而我们的投资决定了不可能支持那么长的周期。” 再比如移动镜头,整套设备运进去就至少需要请10个民工,所以摄制组的移动镜头拍摄基本上靠的是人力,在两棵树中间拉一段绳子,摄影师放个架子坐在上面,像溜索一样滑过来,可以达到非常相似的拍摄效果。 还有航拍,国外拍摄这样的片子动辄就使用直升机,但陈晓卿算了一笔账,直升机使用1小时要6万元,完成一次拍摄要30万元,还要等天气,因此整部《森林之歌》的拍摄仅动用了两次直升机航拍,陈晓卿就再也不敢打这个算盘了。 但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编导们还是不辞辛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初来做培训的外国专家看过片子后赞叹地说,第一次,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镜头四:交错在遗憾与理想之间……
《森林之歌》并不是最好的自然类纪录片,它是一个命题作文,很难用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对森林的观察,实现一个个性化的解读…… 尽管《森林之歌》的拍摄基本上达到了陈晓卿的预想效果,但如今回味起来,却还有着或多或少的遗憾。遗憾有些是自然条件造成的,也有些是人为造成的。 比如讲红树林的那一集,红树林本来是一个被损害的守护神的形象,但是因为拍摄期间的一年都没有刮台风,故事中最动人的东西就没有体现出来。再比如有一个镜头拍的是蚂蚁把胡蜂抓住杀死,由于编导的敏锐性不够,没有成功地捕捉到蚂蚁抓到胡蜂的那个镜头。 陈晓卿说,作为一部试水的作品,《森林之歌》还有着广阔的发展和进步的空间。他理想的自然类纪录片,应该更灵动一些,更解放一些,充满了个性色彩。他非常喜欢去年上海电视节获金奖的一部法国自然纪录片《Jaglavak》(《红蚂蚁》)。Jaglavak是非洲的一种红蚂蚁的名字,它是白蚁的天敌。故事说的是在一个小村庄里有一户农民,家里房子的木头都被白蚁啃光了,为了驱除白蚁,他请人在房间里洒满了防治白蚁的药物,可是没有用。无奈的农民只好请巫师来作法,祈祷Jaglavak神灵的佑护。最后,农民自己在田野里用帽子兜了一群Jaglavak回家,然后和儿子充满兴味地坐在那里,看红蚂蚁大战白蚁。 “虽然是一部自然类的纪录片,却用非常人文的视角切入,充分展示了当地的民俗风情和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人文环境,并且它的主题非常博大,不会集中在某一个固定的点上,让人深深思考。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但解决困难的方法可能会有很多,那么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能不能找到自己的Jaglavak?”
●镜头五:回响
我的一生都充满着阴差阳错,上学的时候,本来想做一个文字记者,就因为我个子高又不近视,把我调到摄影系去了,而我在那之前连相机都没摸过。后来我成为了一名摄影师,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部片子没有导演,我就被抓来充数当了导演。就好像一条生产线,原先是生产肥皂的,结果一声令下说,不能生产肥皂了,要生产方便面,没办法,就学着生产方便面吧。就这样,先是做现实题材的纪录片,1996年开始做文献题材的纪录片,2000年又开始做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几乎纪录片中能够涉及到的种类我都做过了…… 尽管陈晓卿自嘲自己的人生是身不由己,但是在这样身不由己的人生中,陈晓卿仍然过得有声有色。当年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的时候,陈晓卿有过一个愿望,就是要拍一辈子片子。如今人到中年,看来这个愿望倒是实现了。作为《见证·影像志》的制片人,陈晓卿现在已经不再亲自掌镜,但令他深感欣慰的是,自己带出的徒弟都已经青出于蓝。看到这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陈晓卿总会想起青葱岁月时的自己,不过现在的他在面对作品的时候,已经少了一分年少轻狂的冲动,多了一分冷静、自制与深沉。 “年轻的时候拍《龙脊》,看到那些孩子读不起书我也跟着哭,看到一个民办教师临死前告诉自己的女儿要子承父业,我也感动得流泪。而如今,我会想到他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有对职业的执著与忠诚,还有对女儿将来失业的忧虑,从而力图向观众展示一个开放式的、多元化的思考空间。《森林之歌》也是一样,老猴王死了,它的太太很伤心,这样的情感宣泄就跌入了爱情至上的固有模式,并且猴子的动物性永远大于它的社会性,而最后实拍的结果也证实了,它又重新适应了新猴王的家庭。”陈晓卿就这样,将他对纪录片的领悟和感受,毫无保留地教给自己的徒弟。不仅如此,如今的陈晓卿还有着一个新的目标,他正在酝酿一个电影剧本,等待着下一个机会的降临。 时光在讲述中匆匆流逝,黄昏的阳光透过窗子照在陈晓卿身上,他似乎也成了纪录片中的一个人物,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明暗错落的清晰剪影…… |
|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